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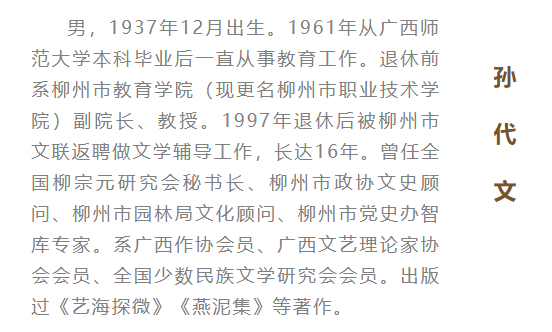
今年除夕前,女儿接我们老两口到她位于保利小区的家中过年。此时正值全国人民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刻。在宅居保利足不出户的日子里,我们悄悄地度过了结婚56周年的纪念日。虽然我向来对结婚纪念日和祝寿之类的事了无兴趣,但是我和老伴经历半个多世纪所发生的人生故事,还是难以忘怀的。陶渊明诗云:“此中有真意,欲辨已忘言。”趁我这年逾八旬的老人,身体还硬朗,头脑尚清晰,还未到“已忘言”的程度。追忆并记叙那些陈年旧事,权当聊以自慰吧。
我祖籍福建彰州府诏安县。清嘉庆年间迁徙到广西鹿寨金鸡村。孙氏家族虽称不上富甲一方的豪门,却也是“堂前椿萱常吐秀,屋后桃李正芬芳”的兴旺殷实之家。听长辈说,族谱载“文成凤有祖,世代永安康”十代,按序列我属“代”字辈,是孙家第六代传人。我一九三七年出生,祖父为我取名孙代文,乳名质彬,是源于孔子《论语》中“文质彬彬,然后君子”的含义,是寄予了很大希望的。我祖父是读过古书的。记得小时候,我家隔壁住着一位随口能歌的远近闻名的歌手袁奶奶,祖父有意考考她,便教我唱首歌去问她:“袁老奶奶好歌王,我今盘问这一行:子钓不纲在哪里,一不熟悉在哪行?”当时我压根儿不懂歌词的意思。祖父早已故去了,直到我上了大学,读到《论语》中“子钓不纲,弋不射宿“的句子时,我才恍然大悟,原来祖父是用表现孔子爱心的典故去考问她的。好在袁奶奶聪明过人,她巧妙地回答道:“你称歌王不敢当,唱歌原为表衷肠;子钓不纲行处有,最不熟悉丧天良。”这事虽过去了几十年,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一九四四年冬,日寇侵犯广西,兵燹祸连。时年我七岁,目睹日寇在麻厂疯狂扫射,血肉横飞,残杀同胞的罪行,其悲惨情景,至今回顾仍有些后怕。日本投降后,还未能过上几天安稳日子,一九四六年春,霍乱肆虐,死者相枕,我父亲就是染上瘟疫而丧命的。亏得我母亲,她一人担起抚养我姐弟四人的重担。母亲日夜操劳,终于在日寇烧毁的旧宅上盖起了新房。哪知祸从天降,新房被恶霸林秀山强占用来开赌场。孤儿寡母,投诉无门。母亲将两个姐姐嫁出后,只能靠租房栖身。为着生计,她长年在外经商,由小保姆郭姐照看我和弟弟。租屋仅有10多个平方米,除了两张床,什么家具都没有。晚上一盏水火油小灯,放在装有衣服的木箱上,没有桌椅,别说写作业,连看书的地方都没有。日常生活更简单:郭姐经常煮一碗头菜蒸在饭锅里,这就是我们的“佳肴”。我和弟弟从没有吃过早餐,至于什么牛奶、面包之类,别说吃过,连见都很少。因为过惯了这种清苦的生活,所以至今还多少残留着“过得去”、“将就”等习惯。如今生活好了,衣食无忧,女儿常劝我们饮食要讲究质量,不要吃剩的饭菜,生活用具要更新等等。真是“事非经过不知难”啊。尽管童年生活清苦,但我能苦中作乐。我家对面是桂戏院,我常偷溜进去看戏。前朝后汉的戏文,给了我文化滋养和精神享受。
解放了,生活有了新的希望。被林匪霸占的房子,终于回到了我们手中。一九五一年我小学毕业后,考上了柳州龙城中学。尽管当时龙中的学费比较昂贵,母亲仍全力支持我上学。我在龙中读书时,生活较安定,母亲除了给我伙食费外,还给我零花钱。有时还带我到餐馆吃饭。放暑假时,她把我带到亲戚家,跟一个读高中的少忠哥学见识,那段日子真令人开心。谁知好景不长,暑假时我和母亲乘车回家乡,当时法制不健全,母亲不明不白身陷囹圄。这晴天霹雳般的沉重打击,把我和弟弟推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。就在这紧要关头,我的姨父姨母将我两兄弟收养到家中。接着我到龙中办理转学到鹿寨中学的手续,开启了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段不寻常经历。
我两兄弟寄居在姨母家中,给他们带来了较重的负担。姨父以农耕为主,收入不多。我两兄弟的到来,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。好在我姨父姨母是极有爱心的大好人,他们对我两兄弟视同己出,从来没有半点嫌弃,同甘共苦,我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时至今日,我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们。他们是我的再生父母,是我的救命恩人!可惜他们过早地故去,我无法报答他们,每思往事,令人痛心不已。
一九五四年我初中毕业,考上了柳州高中。姨父姨母倾其所有,想方设法筹钱让我顺利地上了高中。在高中时,学校发给我每月六元的乙等助学金,基本上解决我的吃饭问题。可是到了高中二年级时,家里实在支撑不下去了,穷得连供我乘车到柳州的车费都没有。无奈之下,我只好向学校呈上休学报告。就在这困难关头,得贵人相助。柳高彭校长托人转告:只要我能来学校,就可提高助学金等级,解决我的伙食问题。还有我同学张绍周的母亲梁伯母,她资助我几块钱,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。就是在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下,我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上大学。在我经历了这人生道路上的拐点之后,我深深懂得,“知恩不报枉为人”的道理。
柳高是名师荟萃的学府。在老师精研问学的影响下,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。一九五六年,报上正开展电影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的讨论。一位名叫白玉栋的作者,认为影片中主人公张忠良的堕落变质,是环境诱惑所致。我不赞同他的观点,就给《柳州日报》写了篇商榷的文章,指出张忠良的变质是他思想意志薄弱造成的,这才是矛盾的焦点。文章发表后,给了我很大的鼓舞。从此,一发不可收,又写些短文在柳州报发表。高三时,一位外语教师以课程同步为由,在课堂上闲扯故事。对此不当做法,我以《俄语课与威尼斯商人》为题,写成小品文寄给《广西教育》杂志社。文章发表后,受到班上同学的称赞。高中毕业,我报考文学专业以至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坚持文艺评论的写作,这与高中时爱好文学有很大的关系。
一九五七年秋,我母亲已从农场回家。正好我考取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,过上了包吃、包住,每月还有几元零用钱的安稳生活。
刚进大学,正逢开展反右斗争。在揭批右派罪行的运动结束后,我们新生才正式上课。课余的政治学习,系党支部要求我们这批未参加过鸣放的新大学生,检查思想,向党交心。把自己那些不正确的、错误的甚至肮脏的思想言论,毫无隐瞒地向党交待,以表示对党的忠诚。就在这种“左”的思想引导下,大家都写了交心材料。我把自己写的交心材料装钉成册,冠以“忏悔集”之名交上去。想不到,这册交心材料被放进档案里。“文革”开始,某些居心叵测的人以此作把柄,把我的交心材料当作反党言论公之于众,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,遭到残酷的迫害,长达七年之久。一九七二年,落实政策,我获得解放,恢复了名誉。回顾这段历史,至今仍心有余悸。
一九五九年秋,在师院图书馆工作的老乡家里聚会,认识了我现在的老伴蒋继兰。虽说我和她同在鹿寨中学上学,但只闻其名,并不相识。她是个学霸,记得有次段考,她以各科平均成绩95分,获得全校第一名,受到表扬。初次见面,她身穿一套蓝士林衣裳,身材小巧,面目清秀,一头齐耳短发,言语不多,显得矜持、诚朴。聚会完了,我和她一同步行回中文系。边走边谈,她说:“这次高考不理想,我原来许下‘西大非吾愿,北大方可期’的雄心,算是落空了。”我安慰她说:“师院中文系有许多全国知名的教授,只要认真刻苦地学习,还是可以学到很多知识的。”我还说:“我读了两年大学,深感要读的书太多了,远远达不到老师的要求。”临分手时,约定今后多交流,我愿意把课堂笔记借给她看看。从此之后,我俩从相识到相知发展到相恋了。
平时我们各自忙于学习,只有到了周末才相会。虽然我和继兰确定了朋友关系,但我还不敢在公开的场合去找她。所以,每个周末约会,总是在晚饭时的饭厅悄悄地告诉她。约会的地点,选择在市中心的三多路口的书报亭。我俩沿着环湖,边走边谈,天南地北,什么都聊。她文静笃学,真诚待人,在困难时期,就表现出来。1960年,我们年级到龙胜捡茶籽。由于营养不良,许多同学患了浮肿。就在这紧要关头,她想方设法托人给我捎了一瓶茄子辣椒酱。雪中送炭,帮我渡过了难关。此后,她又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饼票送给我。我们的爱情,就是在相濡以沫中建立起来的。寒假我和她一同回家,我把和继兰的关系告诉母亲。母亲听了很高兴。她觉得继兰确实是个知书达理、贤淑本分的好姑娘。
寒假期间,读了系主任蓝少成老师发表在《广西文艺》上的《批判继承要同时并行》的文章,感到文章的观点有些偏颇。于是,我和同学罗会祥联合写了一篇题名《也谈‘同时并行’》的商榷文章,寄给《广西文艺》。1961年春,我们到南宁作教育实习时,想不到文章发表了,并引起争议。围绕如何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问题,《广西文艺》开展了长达半年的讨论。通过这次学术争论,焕发了我们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的学术勇气。
教育实习结束回到学校后,就在我们全力投入撰写毕业论文时,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一天中午,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姑娘来到宿舍楼找我。她自报家门说:“我叫钟素玲,是隔壁工人医院的医生。受同事小邹之托,请你到她那里商量事情。”她说的同事小邹,就是我当年读龙中时的老同学。记得我来师院上学时,还跟她一起聚会过。她会有什么事情找我呢?我将钟女士送下楼时,心里一直在琢磨着。晚饭后,我换上一套整洁的衣服,来到医院的牙科室。小邹笑容满面地迎上来,招呼我坐下。她身材高挑,举止大方,白色的衬衣配上笔挺的咖啡色西裤,显得年轻、漂亮。我们边喝茶边谈,她询问我许多老同学的情况,全然不提要商量的事。事后我才明白,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这次主动出击,就是试探我对她是否感兴趣。临别时她送我到门口,并约定下次见面。此后,她领我游榕湖,登叠彩,探龙隐,宛如一对恋人。小邹的插足,弄得我神魂颠倒。我喜欢小邹,又不忍抛弃继兰,使我陷入两难的矛盾境地。临近放假时,我约了继兰,沉痛地向她坦白了我的背叛行为,请求她原谅。继兰听完了我的陈述后,沉默了好一阵,最后她抛下一句话:“你的轻狂是不可容忍的!”就气冲冲地走了。后来放假她来到我家里,她很有涵养、平淡地对我母亲说:“伯母,有件重要的事,等代文回来跟你说。”说完,她就回寨沙去了。
究竟是什么事呢?母亲也猜不透。直到我接到分配去桂林师专任教的通知,我带着小邹回到家,她才明白。母亲表面上不动声色,热情款待客人。在送走小邹之后,母亲才严厉地批评我。说我做事不稳重,继兰这么好的人,为什么不要她?几十年过去了,现在回想起来,如果不是母亲慧眼识人,坚持非继兰莫属的决心,尤其是当师专解散,我调到柳机工作后,她不辞劳苦,几次上到桂林劝说继兰,向她赔不是,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继兰被感动了,才答应跟我重修旧好,弥补了我当年犯下的重大过错。
一九六一年秋,我到桂林师专报到。学校分给我一个单人房间。此时小邹充分发挥了她办事精明的特长,为我精心布置房间。她买来了台布、石膏塑像之类的装饰品,营造了温馨的环境。可是,一件出人意料的事,让我断绝了与她的关系。一天晚上,我没有和她打招呼,独自一人来到她住的单身宿舍。推门一看,只见床上睡着一个人,床前摆着一双布鞋。我顿时头脑轰鸣,像雷击一样,不问青红皂白,怒气冲冲地转身走了。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与小邹联系。小邹莫名其妙,她多次来信询问缘由,我既不回信,也拒绝和她见面。事后得知,那是一个大误会。那天是她母亲从家乡来看望她,在床上歇息的,正是她母亲。现在回想起来,由于我的轻率举动,给小邹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时至今日,我还无法表达对她的歉意。这也许是天意吧,如果没有那场误会,我的人生道路是难以想象的。
在桂林师专,我文思泉涌,不畏权威,连续撰文在报上与他们争论。不久师专解散了。在等待分配期间,我来到柳州寻找接收单位。就在这为难的时候,我表弟蔡文雄向我伸出援助之手。他妥善安排好我的食宿,让我专心去寻找单位。我跑了几个部门,都无功而返。正在无望之时,有人提议到柳机学校去试试。当我顶着烈日,汗流浃背地赶到柳机子弟学校时,想不到王厚麟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他非常欢迎我到他们学校任教,并表示只要我同意,他可以派人到桂林师专直接办理调动手续。王校长一番诚恳的谈话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我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。不到半个月,一九六二年八月,我顺利地调到柳机子弟学校工作。第二年,学校领导对我关心备至,不但分配给我一个大房间,还把我母亲的户口从鹿寨迁到柳机,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。我一九六二年到柳机,直到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一九七六年调离,整整待了十五年。柳机是我人生道路中一个重要驿站。我在此结婚生子,建立了家庭;结识了志趣相投的挚友,创作发表了不少作品。尽管“文革”中我受到很大的冲击,但至今我仍无悔于当初的选择。因为柳机人诚实厚道、坚毅善良、主持正义的高尚人格,给了我鼓舞和力量。我离开柳机虽已四十多年,但与柳机的情谊至今仍保持着。记得在“文革”中我受到批斗的严重关头,是工人师傅为我解难,是干部为我报讯,是学生为我排忧。总之,柳机干部职工对我的情意,我是没齿难忘的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,我调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母校柳州高中。踏进柳高校门,浩劫后那棵浓荫覆盖、枝叶婆娑的大榕树依然挺立。沐浴着党的阳光,柳高又扬帆起航了!教师恪尽职守,精研奋发,挑灯夜战;学生勤学好问,比肩争锋,废寝忘食。那种弦歌书声又回荡在优美的校园里。春雨滋润,桃李芬芳。大批莘莘学子跨入大学校门,不负百年名校的培养。我在柳高工作八年,入了党提了职,奉行尊师重道的传统,见证了名师善教,学生善学的良好校风。一位姓刘的班主任,为了学生的成长,他呕心沥血。他有一本学生日志,不仅详细地记录了每个学生的学业成绩,还对学生的家庭状况、兴趣爱好、奖励表彰、病事假条、友朋联系及心得体会等情况,几乎记录殆尽,就像是一本完备的学生档案。他对学生情况了如指掌,有一年,一个正在参加高考的学生,刘老师得知她父亲急病住院的消息,他立即赶到医院与她家人商量,决定暂不告诉这个学生,让她安心考试。待她考试完毕填报志愿后,她的父亲已去世了。为了宽慰这位学生的情绪,刘老师组织班干陪这位学生一道回家吊唁,就这样妥善地化解了这一偶然事件。
柳高学生的聪颖善学也很突出。某年,一位姓戴的学习尖子,历来考试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。可是,在一次临高考前的模拟考试中成绩下滑,跌至十名之后。老师焦急而戴同学则若无其事。老师找他谈话,才得知这是他采取的策略。为了检测自己的记忆能力,他一星期不碰书本,花时间进行体育锻炼。模拟考试后,他拿试卷与课本作了对照,归纳出哪些知识是因自己记忆模糊而需加深之处。结果,他考取了清华大学,成了学校理科的状元。
一九八三年,我奉调去筹办西大分校,从此离开了我眷恋的母校柳高。为筹建新校,日夜奔忙,不辞劳苦。跟随白发丛生的老校长,挥洒汗水,奋战在工地上。“马鹿山下摆战场,千军万马辟大荒。誓教高楼拔地起,胸怀壮志迎朝阳。”春风秋雨,盛夏寒冬,在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下,广西工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了。一九八七年,我调到柳州市教育学院,又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。
“好风频借力,送我上青云。”这是我在教育学院工作十载的状况。一九八八年,我被任命为副院长,先分管后勤,后管教学,兼上美学课。学院和谐的环境、友好的氛围、便利的条件,提升了我的教学和研究水平。成立柳宗元研究所,我亲任所长。拨经费、买资料、定课题、写论文,营造了一股研究的氛围。促进了与外界的学术交流。教学上,建章立制,鼓励竞争,褒奖创新。结果取得了教学和研究的双丰收。我荣任全国柳宗元研究会秘书长之职,又获得全国曾宪梓教育基金教师三等奖的奖励,还被选为鱼峰区人大代表。这种种荣誉,坚定了我“生命不息,奋斗不止”的信念。
一九九八年,学院在返聘一年后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。紧接着柳州市文联柯天国主席聘我为辅导员,为我提供了极为宽松优越的工作条件,使我如鱼得水,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。我们下厂下乡,体验生活,搜集素材;开办培训班,举办作品研讨会;参观革命圣地,采访抗战老兵,撰写报告文学。就在文联提供的平台上,我出版了文艺论集《燕泥集》;荣任了市政协文史顾问,充当了十届散文大赛评委,担任了市教育局百家讲坛主讲,市电视台摆古栏目顾问及市政府筹建文庙专家组成员。“莫道桑榆晚,为霞尚满天”,我晚年能发挥些余热,做成些事情,应当归功于文联组织对我的提携与帮助,我从心底里表示感谢。
我能在文联工作十六年,还得感谢老伴的支持与帮助。她身患糖尿病,既要操持家务,还得照看我病卧在床十一年的母亲。尽管请了保姆,她得经常协助保姆替母亲擦身、洗澡、喂药、换尿片,甚至还委身用手帮母亲掏粪便。作为一个媳妇,她竟能做亲生儿女都做不到的事,怎不叫人感动呢?
回顾老伴这一生,为儿女和家庭付出太多,我确实亏欠她。在读大学时,在感情上,我曾伤害她,而她宽恕了我;她大学毕业分配到市一中任教,也不嫌弃我在郊区,乐于与我成婚;“文革”中我受到迫害,身处逆境,她忠贞不渝,毫不动摇;在坏人抄家,她被捆绑时,她大义凛然,毫不示弱;“文革”结束后,她潜心教学,辅导学生,担任学报编委,积极撰写论文,参与学术讨论;退休前,她母亲中风瘫痪在乡下,在完成艰巨的教学任务后,她每个星期天都不顾疲劳乘车前去照看;当我母亲被送回老家养病时,长达半年,她陪我每个星期天乘车去看望,毫无怨言。她为人真诚、善良,曾私下资助保姆,从不外说。时光流逝,岁月悠悠,如今她虽已步入耄耋之年,身体虚弱,步履蹒跚,却坚守初心。我对老伴,无以回报,只有竭尽全力,悉心呵护,“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”。
2020年4月15日
 微信公众号
微信公众号



